以具体电影为例,看屏幕电影发展至今,有何媒介特性?

多视窗的视觉呈现是屏幕电影的一种独特语法。“分屏”的影像形态,突破了传统电影中惯用的“单画框中的单影像”,转而强调多界面、多信息流的并置与共同在场。
在《弹窗惊魂》的13-15分钟内,屏幕上共分出了5个并置的信息窗口。此时男主角尼克的电脑刚刚接受了黑客传递给自己的超链接内容,因此他成功获取了对偶像的监控视角。
在整个屏幕上,左下角是尼克此前使用过的截屏软件,软件中整齐排列着无数张女明星吉尔在活动中的截图;左上角是女明星吉尔新电影发布会的直播页面,此时显示直播已经结束。中间是尼尔正在面对镜头与黑客进行沟通的界面;右上角是黑客成功获取的对吉尔手机的监视窗口。

在此时,不同时空以框型为边界的赛博视窗空间的画面内容被呈现了出来,并由此组成了两条人物行动线,以及无数个信息点与多个视角,在一个屏幕之中迅速建构出了复杂且极具张力的影像情景。
为了能够缓解大量信息流涌入叙事中,屏幕电影通常会采用焦点强调的方法。比如在《弹窗惊魂》中,当大量的信息被并置,往往会将主要信息放大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分屏”呈现的是数字化图像的多个独立图层结构与传统电影视觉艺术的一种有益的融合,使其成为了屏幕电影影像建构的一种核心方法。

在早期还处于探索时期的《梅根失踪》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并置的画面展现梅根与好友线上对话的状态,到了后期屏幕电影的代表作品《网络迷踪》、《解除好友》中,也都在不断采用此类画面建构,展现多个人物之间的对话状态。
在屏幕电影中,通过点击、拖动、叠加、关闭、切换、并置、刷新不同的超链接内容,形成一种多元并置的超空间。
屏幕突破了空间限制,场景之间的距离被悬置。“在场”有了全新的法则,屏幕自身即可完成空间调度,例如《弹窗惊魂》的开篇始于一场电影发布会,但是随着画面不断地收缩,观众会发现,原来刚刚多看到的发布会的现场画面其实来源于一个电脑网页。

随后,“电脑的使用者”打开了邮件页面,并点击了其中的链接,紧接着“电脑使用者”的形象占据了整个画面。当画面再次收缩后,整个屏幕便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即发布会的直播空间与电脑使用者所在的房间的空间。
同时“并置”的窗口也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流。并列放置各种意义单位,使得其在文本中取得连续参照,将文本的统一性存在于空间关系中。例如在《网络迷踪》中,在大卫寻找女儿线索的过程中,找到了女儿在直播平台上曾经保存的多次直播的视频记录,他开始不断点击不同的直播内容试图弄明白女儿在网络上的社交状态。

此时大量不同时间段的视频内容被并列放置在了同一空间中,打破了叙事的单一线性时间流。同样的,在《双重预约》中,男主雄二为了能够周旋于两个女性之间,他求救自己学IT的好友为自己录制了一段万能应答的视频,来应付视频对面的女性。
当他将已录制好的视频拖拽到对话框中时,屏幕上即同时并置了此前已录制好的雄二的视频画面与当下正在摄像头前操作电脑的雄二画面。
因此,从以上时空的关系来看,屏幕电影蒙太奇已然在空间中电影画面之间的位置关系这一新的维度上展开。时间变得空间化,分布于屏幕上,可以看作是用于多任务、多窗口的图形用户交互界面美学。而这背后,则是数字时代的加法与共存逻辑。

例如在《双重预约》中,女孩点开了储存着大量不同时期雄二照片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实际隐喻着无穷的文本与信息。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我们身处于同一时代:这是一个并置的年代,是远近相互、内容并置的时代……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在时间中发展的漫长生命不如说是一个点与点相联系,各种联系相互交叉的网络。”
因此在屏幕电影的呈现中,历时性维度不再优先于共时性维度,时间蒙太奇也不再优先于单一镜头中的蒙太奇。屏幕电影中文字、符号、图像、音效构成“表征的汇聚”。在传统影像中,这些抽象符号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在屏幕电影中,这些符号则承担了传达情感、制造悬念、渲染氛围的功能。

在点开页面进行信息的传输的过程中,观众可以通过操作者对于信息符号的选择,输入时的停顿、修改或是删除来获取操作者当下的内心状态。例如在《网络迷踪》中,有多次展现父亲在与女儿聊天时更改所输入的文字内容与标点符号的情节,以期塑造出不善言辞的单亲父亲与青春期女儿之间微妙的父女关系。
反复输入的情节,充分刻画了一个父亲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父女关系,他一方面生气于女儿的不告知,另一方面又不想轻易同女儿发火。而观看者大量的“屏幕生活”的经验,也使得计算机自身的系统功能符号往往能够变为特殊的表意符号。

例如开机、关机、加载、黑屏等等,其实都意味着叙事的中断或是开启,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影片故事节奏。在《巢穴》中,影片开头即是经典的计算机内容加载的符号,这一设置一方面标志着影片中主人公的电脑开启,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整个电影的开端。
在《夺命连线》中,也使用了Zoom这一聊天软件的开启界面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始。而电脑故障作为一种独特的屏幕修辞手段,能够轻易唤起现实观众在实际操作时面对故障所感受到的焦虑与不安的情绪,因此,在叙事中加入画面故障的情节,能够渲染出危机的氛围。

例如在《巢穴》中,当黑客第一次入侵女主人公的电脑时,就出现了电脑闪屏这一画面。当女主因为陌生女性的惨叫从睡梦中惊醒,快速跑向自动打开的电脑时,此时虽然连线中的女性凄惨的叫声已经停止,但是屏幕画面却再次出现故障的闪动,暗示了接下来的情节将会愈发危险。
数据库逻辑下的屏幕叙事
在马洛维奇看来,文学艺术与电影艺术都强调叙述,长期以来,叙述通常被视作现代文化表达的主要形式。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一个与计算机密切相关的概念——数据库出现了。纵观当下人们使用的新媒体对象可以发现,本质上这些新媒体并不进行叙事,它们不存在“开端”或是“结局”。

就如同当下人们不断向下刷新,无止境浏览着APP一样,这些新媒体对象,显然不具有“结局”。同时每一个被浏览的视频都具有同等的地位,记录着不同发布者的生活状态。在现代计算机科学中,“数据库”即数据的结构化集合。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分别使用不同的模型来组织数据。马诺维奇把数据库视为计算机时代的全新符号形式,它代表着构建自身体验和世界体验的一种全新方式,并在新媒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数据库与叙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马诺维奇认为:“人们在新媒体中创作作品,实际可以理解为,在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新的交互界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交互界面提供了访问数据库的途径。”推至屏幕电影,即在《网络迷踪》中,父亲通过登录已经离世的妻子的电脑账号试图寻找关于女儿的信息。
他点开了一个文档,其中包含的是关于女儿的不同朋友的个人信息与联系电话。随后通过父亲的不断地的点击,他最终找到了女儿曾经好友家长的联系电话,即获得了推动剧情继续发展的信息。

更直白来看,在《双重预约》中,男主雄二在为了能够在与女生的交谈中展示出自己的博学,他在与女生视讯的同时,不断点击着Google页面,通过实时的搜索寻找女生所提出问题的正确答案,他的每一次搜索,界面上都会出现全新的信息。
当然,观影过程中作为观看者并未直接在数据库的记录中进行检索等一系列操作,但是本质来讲受众是以另一种形式参与到了一系列行为和认知过程中,以自身的新媒体使用经验为基础,同影像中的主角进行了搜索、点击等行为。

从历史上看,艺术家创作作品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媒介中,因此,交互界面与作品等同,例如雕塑、传统画作等。但是在新媒体中,作品内容与交互界面往往会形成一种分离的状态,因此,新媒体的作品中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通往多媒体材料数据库的交互界面。
从这一角度可以重新看待数据库与叙事之间的对立关系,并重新定义叙述这一概念:即交互式叙述可以看作浏览数据的多个轨迹总和,传统的线性叙述实则是众多轨迹中的一种特定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任意一段数据库的记录序列都能够被称为叙述。文艺理论家米克·巴尔(MiekeBal)将叙述定义为:“叙述理应包含有一个演员与一个叙述者;同时也应包含文本、故事、素材这三种不同层次;它的内容应该是由演员引发的或经历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时间。”
因此作者需要能够掌握好元素的语义与其中的逻辑,才能够使自己所使用的对象满足以上的标准,进行完整的叙述。当下,屏幕电影作为电影艺术与计算机文化融合的最为典型的电影形式,其背后的数据库逻辑尤为凸显。

经典的叙事电影一般遵循因果轨迹,选择以视线剪辑为主导的缝合体系。但“媒体界面”的出现破坏了可以产生“无缝”的叙事空间和时间的经典缝合机制。在屏幕电影中,许多镜头视点不再属于影片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的主观观看视点。
例如在《网络迷踪》中,男主在弟弟家安装的摄像头所拍摄的客观画面即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弹窗惊魂》中男主点击了超链接后,突然出现了摄像机自动拍摄男主的画面,并占据了整个屏幕。

显然以上这些镜头不是为了让观众认同片中角色在主观层面上的观看视角,实际上是呈现为摄影机在客观层面上的观看,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无法辨认的抗拒缝合的凝视。
热奈特(GérardGenette)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种:无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在屏幕电影中,叙事聚焦呈现出内外融合的特点,掺杂主体与客体的凝视。一般来说,内容聚焦叙事直接体现为第一人称视角,侧重于呈现人物的见闻及思想意识。

例如在《巢穴》中,女主的好友收到了黑客冒充女主发给自己的信息,于是她一边拨打着视频电话一边前往女主的家中,在房间里来回寻找着失踪的女主。此时画面呈现的即为好友的聚焦视角。
在这样的叙事视角下,观众的视角受到了限制,从而营造出了一种未知的惊悚感。很快,好友在黑客的指引下掀开了被子,点击放在床上的电脑后,电脑摄像头画面随即开启,出现在镜头内的好友身后突然出现了戴着面具的黑客,好友被黑客用木棒击打昏倒。

屏幕电影中采用叙事聚焦内外融合的叙事视角。一方面克服了单一内聚焦视角的缺点,通过屏幕上各类媒介的融合,合理呈现出了外聚焦的视域,另一方面,屏幕电影通过利用摄影机镜头的转换改变观众的位置,使得观众成为屏幕的代理人,而这种代理是将屏幕划归入观众的生活经验中,而非“吸入”进影像序列中。
同时,屏幕中所呈现的视频播放、鼠标移动,都能够给予观众虚拟掌控权,规避内容聚焦所带来的脱离感。而通过对屏幕主体操作过程的实际记录,具象化地呈现出主体内心的感受与想法,也得在内外聚焦融合的叙事视角下,屏幕电影拥有着强大的叙事张力。

屏幕电影中多种应用媒介数据叠加的聚合呈现,天然就是以跨媒介叙事为基础,以内容与介形式的匹配度与相容性为前提,在不同媒介形式的互文生产中形成传播合力,促成内容的衍生与扩张,同时不同媒介通过不同形式的表达,以形成不同的叙事视点。
受众的沉浸感受
新媒体通常期待将主体转化为用户,期待主体与作品中的呈现对象进行交互动作。在马诺维奇看来,“那些网页、电子游戏、虚拟空间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超媒体应用程序,其本质上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时间性动态——在幻觉与悬念之间持续地、重复地来回切换。

这些新媒体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试图不断提醒使用者,它们所具有的人工性、不完全性、以及被建构性。它们一方面给用户以完美的幻觉体验,另一方面又不断暴露出自身潜在的机制。
马诺维奇用早期人们等待网页加载图片的过程来解释这一特殊的时间性动态,而如今当用户使用智能手机进行APP之间的切换时,同样也是这一时间性动态的某种呈现。

传统电影艺术的目的是在呈现中始终维持幻觉的连续性,尤其是当观众静止处于黑暗的环境中却仍然感受到某种脱离时,会使他们失去观影的乐趣。但是新媒体的美学则强调的是一种机制的定期重现,传播渠道在信息中的保持持续在场,使用户并不会沉溺于幻觉的梦幻世界中过长时间。
主体将会在投入与独立的两个状态中实现不断切换。这实际上在计算机游戏中极其常见,当用户操控游戏中的主人公不断向前时,会突然弹出醒目的系统提示,迫使用户进行下一步的选择,用户在此时便不得不点击鼠标,切断自己的沉浸式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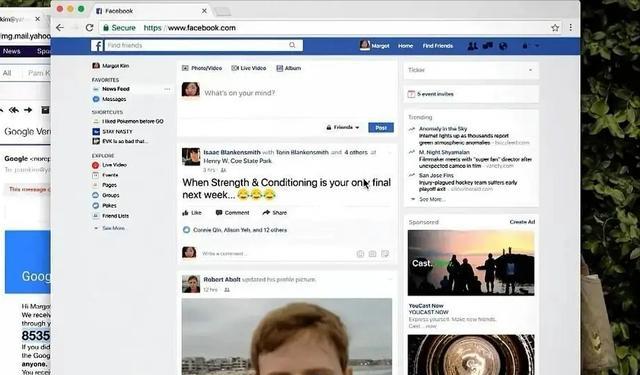
交互媒体的设计师们通常会将主体的时间性体验设计为一系列定期切换的结构,强迫主体在观看者和用户两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在感知与行动之间来回切换,在跟随故事脉络与积极参与故事之间来回切换。
《双重预约》中,雄二在网络上周旋于两个女性之间的设定,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在屏幕电影中新媒体时间性特质的呈现。当雄二在试图与第一位女生进行持续性的约会视讯时,会不断被第二位女生发来的LINE文字消息打断;在视讯画面中,雄二正在对其中的一位女生进行甜言蜜语的攻势,但下一秒,雄二就不得不开始以文字输入的形式与另一位女生进行辩白。

包括在雄二与自己的好友视频聊天,寻求解决约会相撞的方法时,雄二也同时打开着Google页面,在聊天与搜索动作中不断跳转。这种切换在现代主义先锋派戏剧和电影中也会尝试,导演会在作品中强调参与生产幻觉与维持幻觉的机制和惯例。
它会尝试通过演员直视摄影机这一行为,试图撕破摄像机建构出的整个虚构世界,或是让演员面对摄像机直接对话,或是从将镜头后撤以展现片场的环境,以期构建出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一种全新联系。

马诺维奇把这一时间性的切换与传统电影中的正反打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这样的时间性切换实际上是能够将其理解为如同正反打一般的一种新的缝合机制。观众在此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地定期参与到互动文本中去,从而观众这一“主体”可以被插入到文本中去。
具体到屏幕电影中来看,片中主角往往面对镜头,明确观众的“在场”,但这个“在场”并非是间离,而是一种沉浸式的“在场”,是会使观众误认为自己就是屏幕背后的视点,观众与电影中的角色始终保持着一致的视角,在大量数字生活经验的帮助下,观众能够对互联网中的情景产生一种真实性的认同。

在传统影院中,电影作品通过观看模式和闭合叙事体系使观众形成一种对于角色的认同,进而加深沉浸感,而屏幕电影中则依靠大量交互活动为观众带来沉浸感,因为观众需要在整个过程中被赋予更强的掌控感,才能够在幻觉中更为投入。
虽然在屏幕电影中做不到真实的掌控,但是它往往会提前根据观众的数字经验,预估观众面对屏幕时的可能视点,以迎合观众的期待。在多数的屏幕电影中,都会设计屏幕范围内的“推拉摇移。例在《弹窗惊魂》中,由于打开的页面过多,信息比较繁杂,所以大量采用了屏幕范围内的推拉摇移。
聚焦
